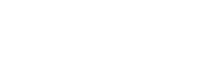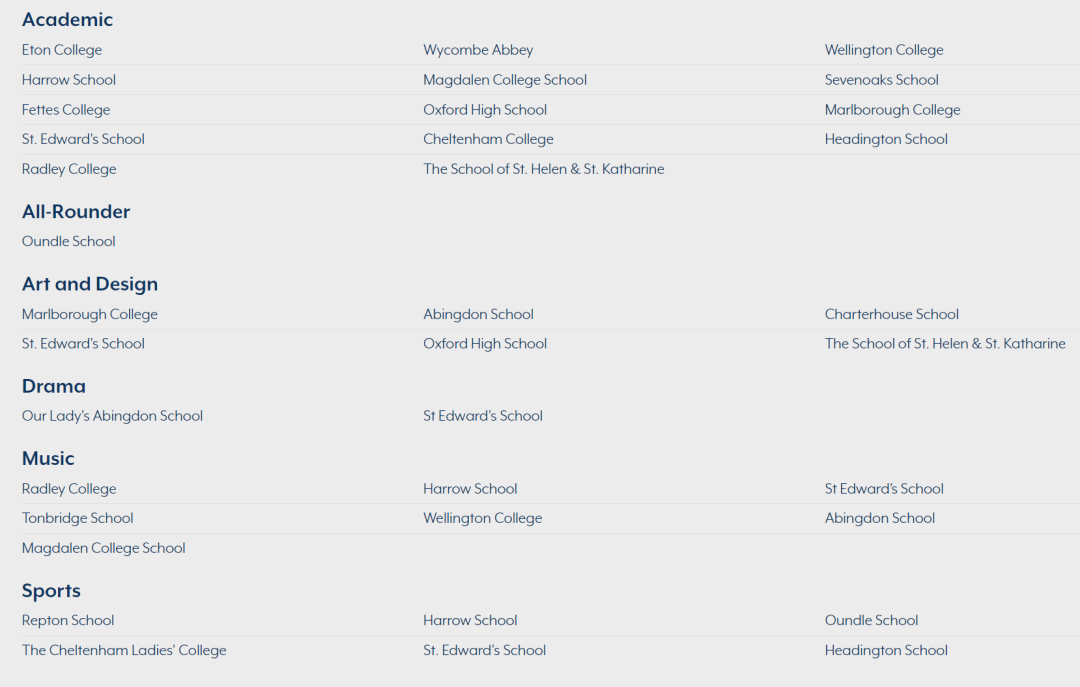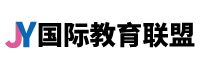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去看电影。这是春天;地上没有雪,但我仍然很冷。我不记得其他细节了。电影是好是坏,剧院里人是多是少,我都说不清——我只记得那天是星期五,因为我们学校有半天课,而我们只有星期五才有半天课。

当我紧张的时候,不像大多数人,我的手不会出汗;他们只会变得寒冷、粘粘,一股寒意蔓延到我的全身,直到我几乎无法呼吸,被冰冷的瘫痪吞没。那天我们就像走在刀锋上一样,刀锋两边都有着无法言说的情绪,我们之间的气氛紧张而又胆怯的期待。一个错误的词,一个失误,我们就有可能跌入浩瀚的未知世界。我被冻结。
我不记得那部电影了,因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只离我几英寸远的手上,偶尔挪到我们一起吃的爆米花里,苍白的指尖上涂满了盐和黄油。我渴望把那只手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我没有做到;我不停地用手掌在我的深色牛仔裤上摩擦,想让我的手、胳膊和胸部暖和起来,因为有一点点摩擦。
电影结束后,我们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傍晚的阳光透过挡风玻璃照射在她的皮肤上,沐浴在白葡萄酒的光芒中,她容光焕发。扬声器里传出一段古老的民谣,一个五十岁的明星用天鹅绒般的嗓音唱着一个女人的故事,与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
最后,是她抓住了我的手,从危险的边缘跳了下去,把谨慎扔给了西风之神,我们一直踮着脚尖走了很久。在青春期,当他们还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眼神天真的高中生时,所有人都渴望听到那些幼稚的话,我们沦陷了。
“我喜欢你”。
她低声说着,就像在黑暗的掩护下低声说着一个秘密,使说话的人充满自信。这句话沉重地落在我的耳朵上,它所暗示的重量压在我的胸口,与我身体里的冰结合在一起,偷走了我肺部的空气。
我吓坏了。
我吓坏了,因为我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人真正告诉我作为一个孩子,女孩喜欢男孩和女孩可以喜欢男孩,因为我的初吻又一巴掌后面对女孩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和上帝,人会说什么?我的父母会怎么说?我吓坏了,所以没有回答。我们静静地坐着,听着那个民谣歌手哼唱着又一次被拒绝的故事。歌曲唱完后,我从她的车里出来,回家了。
从那以后,无论我什么时候和她说话,我的手都很冷。
那天她的脆弱是把双刃剑,我们都以流血收场。对她的话置若罔闻,就像在伤口上留下溃烂的伤口。然而,我们谁也不愿意说话。我们表现得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冷嘲热讽,天真地谈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是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常态——我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一个我们足够大,足够勇敢的时刻,去直面她的表白。
如果她是个男孩,我可能会在那个春天的星期五在她的车里吻她。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手可能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