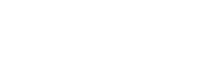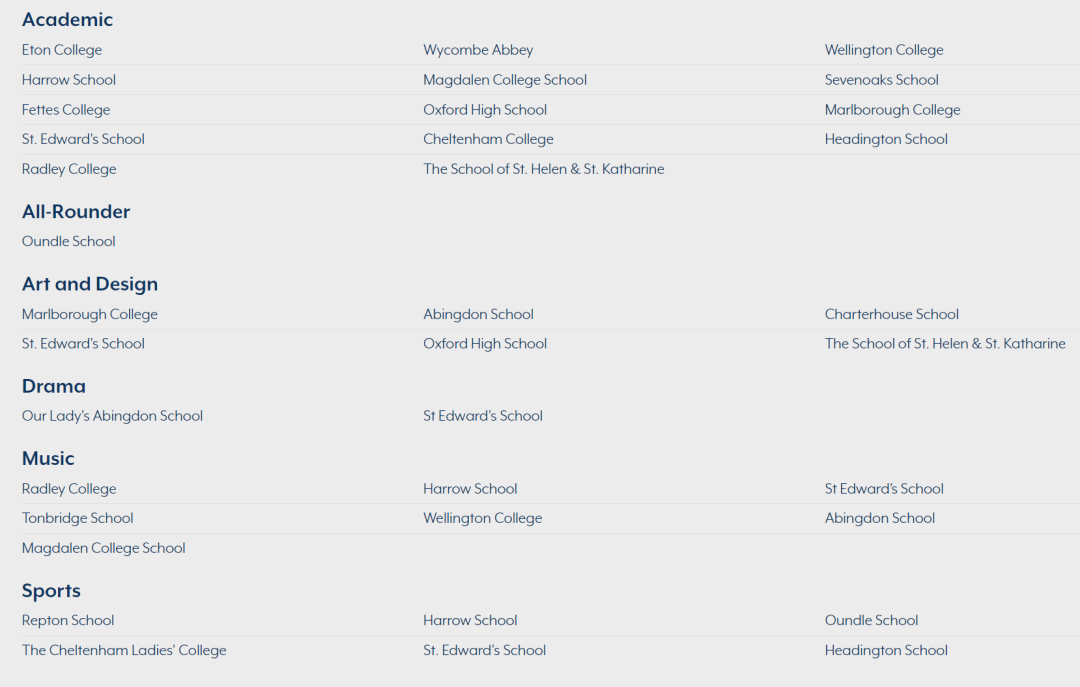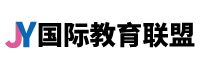我抓住我的内裤,把它们拉下来,看着白色的织物落在我的脚周围。我是裸体;暴露出来。我看着房间另一头的粉红色纸袍,走过去,展开了它完美的对称。我把它裹在我冰冷的身体上,把塑料绳系在腰间。我坐在椅子的一边,从椅子的一端伸出两个马镫,双脚搁在冰冷的木地板上。有那么一会儿,我想知道:还有多少女人不得不穿粉红色的纸袍子?

那位身材矮小、心地善良的医生走了进来,让我躺下。虽然有些犹豫,我还是听从了她的指示;事实上,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人。她17年前生下了我。她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是纯洁的,天真的,无知的;我那双幼稚的蓝眼睛从没见过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现在,我是她的病人,原因我不敢承认。
医生走到椅子的尽头。她准备着一只蓝色的手套。我的脚踩在马镫上,但我的膝盖还在一起。我知道她很安全。我知道她只是在做她的工作,但我还是不想传播谣言。
“我只是去检查一下,确保一切都好。张开你的双腿……”
她掀起粉红纸袍。我害怕;不是关于她,而是当蓝色手套落在我的皮肤上时,我知道那些记忆会涌上我的脑海。不过,我还是照她说的做。自从他以来,我第一次被感动。我知道她是医生。我知道她很安全。《坐在蓝椅子上的女人》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我无法忍受。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回忆来了,我躺在那里,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脑海里浮现的只有他。他可怕的棕色眼睛,他古怪的粉红色运动衫,他危险的手。我低头提醒自己,躺在下面的是医生,不是上帝。
“我必须插入我的一个手指来感觉有没有撕裂,好吗?”
哦,上帝。
“好吧。”
她感觉。我想哭。我可能要吐了。我做不到。
我看见他压在我身上,我的头撞在车的一边,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口,我的手在他身上。
我努力回想《蓝椅子上的女人》会告诉我怎么做。吸气五分钟,屏住呼吸五分钟,呼气五分钟。这行不通……
就像我觉得我再也受不了了一样,她完蛋了。她说他可能撕裂了一些东西,但已经足够长时间愈合了。甚至我自己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不是他。我的身体可以自行修复,但我的心灵无法自行修复。我六个月前就该来了。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该告诉我妈整整一个月我都在内裤里发现斑斑血迹。
我们又聊了聊发生的事。
“你还和他一起上学吗?”
“是的。”
她说她应该做性病检查以防万一。
我又躺了下来。我把脚放了起来。我张开膝盖。棉签进来了。我再次屏住呼吸。
再一次,我想知道:还有多少女人不得不穿粉红色的纸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