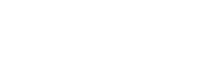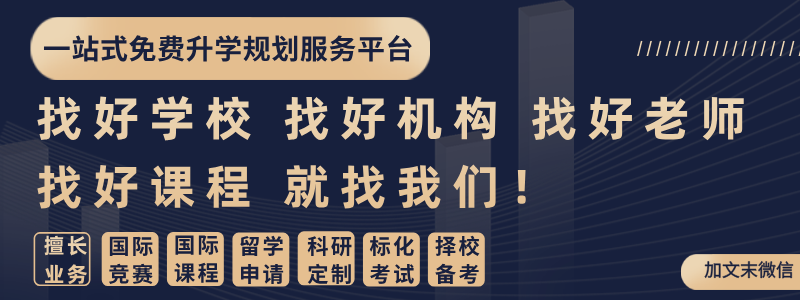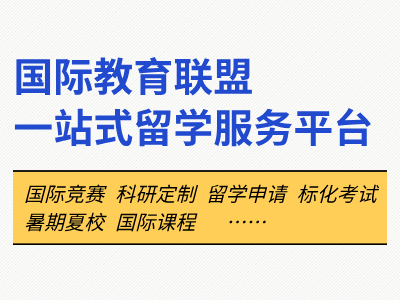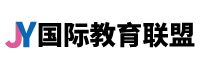2月5日,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宣布将恢复标化考试要求,成为第一所恢复要求申请者提交SAT/ACT考试成绩的常春藤盟校。更新标化考试政策公告的原文如下: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达特茅斯学院将从2024-25申请季开始,恢复对本科生申请者的标化考试要求。
2020年6月,达特茅斯学院暂缓了对本科生申请者的标化考试要求,这是大多数高校为应对史无前例的疫情而采取的举措。当时,我们认为“考试可选”(Test-Optional)政策只是一种短期措施,而不是对标化考试在整体评估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明智评论。
将近四年后,在对标化考试在招生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为学生成功预测指标的价值进行了研究后,我们决定不再延长标化考试可选政策,重新启动本科生入学的标化考试要求,从2029届(2024-25申请季)学生开始生效。
对达特茅斯学院来说,支持我们重新启动标化考试要求政策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底层逻辑很简单:我们相信标化考试要求将提高,而不是削弱我们将最有前途和最多样化的学生引入校园的能力。
原文链接: https://admissions.dartmouth.edu/apply/update-testing-policy
这一决定引发了关于标化考试利弊的又一轮争论,而随着大多数顶尖名校的标化考试可选政策即将踏入生效期的尾声,人们也开始猜测其他名校是否会跟随达特茅斯学院的步伐。
Lee Coffin 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招生和财政援助院长,这个职位是他在2016年从塔夫茨大学加入达特茅斯学院时设立的,多年来他一直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从一开始的紧急暂缓标化考试要求,到后来的一次次延期。去年夏天,达特茅斯学院新任校长 Sian Beilock 上任后, Coffin 表示评估标化考试问题是当务之急。
Coffin 接受了 Inside Higher Ed 的采访,谈到了导致这一决定的原因、他从事招生工作30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他是否认为达特茅斯学院是其他大学重新评估其考试政策的风向标。
以下是对话摘录,为清晰简洁起见进行了编辑:
问 达特茅斯学院是藤校中第一所在关键时刻走上这条路的大学,现下各大学都在重新考虑接下来应该采取的标化考试政策。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一决定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分量的?
答 我们是在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自发地决定暂缓标化考试政策的,从那时候起我们实时地目睹了与我们工作相关的各种规范的转变,无论是在出行上面临的困难,还是校园里的事务,当然还有申请中的各种要素。
如果你把时间追溯到2020年6月,当时我们宣布将暂停标化考试政策,我当时有意使用了“暂停”(pause)一词,因为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是一个临时决定,在疫情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将恢复我们以往的政策。谁知道这个政策会延长了三年之久呢?在这个申请季,我们强烈建议申请者提交分数,因为我们非常重视任何与申请者有关的信息。
我们在宣布这次政策变更的时候非常谨慎,目的是强调我们仅从达特茅斯学院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的教师查看了以往的数据,并就我们的录取流程向我提出建议。我们并不认为达特茅斯学院的这一决定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普遍真理。
我认为有很多学校,比如说我曾经在塔夫茨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工作过,他们这几十年来都推行着标化考试可选政策,而且他们做得很好,这与他们审核申请的方式密不可分。还有一些学校恢复了考试,比如像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看到了标化考试成绩在自己院校内部的合理性,因而重新启动了考试。我认为达特茅斯属于后一类。
问 对你来说,在2023-24申请季建议申请者参加标化考试,而不是像前两年一样采取中立立场,是一种新的做法吗?
答 是的。在2025届、2026届和2027届学生中,我们是“标化可选”的,对每个人的措辞都是:“考试的机会仍然不均衡,因此请根据你们的情况决定是否参与考试。”第三年开始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开始听到高中辅导员说,他们班上的大多数学生都有机会参加考试,但现在的问题已经转变为:“我到底该不该参加考试?”对我们来说,这从来都不是暂停的真正意义所在。当时选择暂缓标化考试要求,是出于对公共卫生和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对测试的批评。
因此,当我们进入第四个周期时,我们的措辞是:“我们建议申请者参加标化考试。”这是我们倾向于重新恢复标化考试政策的一个线索。
问 那么,为什么要重新评估并硬性要求申请者参与标化考试,而不是保留“推荐申请者参加标化考试”的政策呢?
答 去年六月,达特茅斯学院的新校长上任,当时我希望新校长能够在我做出决定之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此,一年前我和她的第一次谈话就是:“这个时刻到来了。你希望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她说:“我喜欢循证政策,所以我们来收集一些数据吧。”她联系了一组研究教育政策的教师,你可能已经看过他们做的研究,这为我们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因此,这条路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对校长说,然后又对教研人员说,这感觉像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招生问题。虽然我们在疫情期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或咨询就暂缓了标化考试要求,但我想确保我们在启动下一步的工作前,能够是进行充分的考量。因此,研究人员的报告强烈建议重新启动标化考试要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证明点。
问 听起来暂缓确实就只是暂缓。恢复标化考试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已成定局?你和大学的其他领导对不同的发展方向持开放态度吗?
答 在我们开始研究时,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onistic)。我没有与任何教师们分享我个人观点。我让他们自己研究,并引导对话。如果他们在研究结束后回来说:“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标化考试可选政策确实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会与所有的校园教师委员会进行对话,并对此进行更多的思考。但我自己有感觉吗?
有的,我的直觉是,标化考试是有价值的。我开始发现,在审核那些没有提交标化考试成绩的申请者时,会不断出现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些信息的缺乏让我们感到不安。因此,在报告出来后,我并不感到惊讶。当我第一次读到它时,我想这与我作为招生官的经历是一致的。
问 几十年来,标化考试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同时你也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
答 从我刚入行的时候就开始了,从我在康涅狄格学院担任招生官时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议。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标化考试是一个持续的话题,人们对此有强烈的分歧。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
问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即使事后看来,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一决定的关键性?此时许多美国大学正在重新考虑其标化考试政策,同时《纽约时报》也对此作出了犀利的评价,这场争论无疑正在重燃,人们很难在真空中想象达特茅斯大学的决定。你是否感觉到,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件事的影响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校园?
答 这个问题应该问我们的校长,但我还是要替她说几句。是的,她肯定看到了一个“领导力时刻”,她想和数据站在一起。我听她说过:“我们以证据为指导,政策以数据为依据。”所以我认为,《纽约时报》一开始就报道这件事,是向 David Leonhardt 已经开始报道的研究发出的信号。我们团队的首席研究员 Bruce Sacerdote 与 David Leonhardt,以及哈佛大学的 Raj Chetty 和布朗大学的 John Friedman 的研究都有密切联系。
因此,在重新激活对话之前,研究人员之间就已经有一个网络。 但我学到的一点是,当你在藤校领域有所作为时,就势必会吸引注意。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词,也不是精英主义,但你不可能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帮助其他地方思考 —— 我们还应该提出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希望的。
当我第一次读到我们的研究时,我觉得最有启发性的发现是标化考试扩大了入学机会这一点。如果没有标化考试,就会造成一种无意的犹豫。我以前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这当然是对的。考试分数这种信息本身不应被视为具有争议性。我认为,在我们的整体和个性化过程中,我们能够确认:“这些分数、成绩单或建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点很有价值。
当然,在疫情期间,我们开始更有意识地关注特定高中的背景。当我们看到学校说:“这是我们的平均分,这是我们70%的范围。”,当我们看到超过75百分位数的分数(这在我们的申请池子中很常见),这就是一个证明点。这有助于我们查看成绩单,然后确认:“好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分数是合理的。”
问 因此,这个结论虽然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但与你在该领域的经验是一致的?
答 是的,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我在塔夫茨大学工作了13年,在达特茅斯学院工作了8年,每年的情况都是,我们申请者的地理中心正离新英格兰地区越来越远。这是令人兴奋的。我看了看今年达特茅斯的申请总人数,65%的申请者居住在美国南部或西部,或者他们是国际生,这是一个历史新高。
随着申请者向不同的地理方向移动,我们也收到了来自新高中的申请者,更多的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都接近全A,这固然很好,但这本身并不能帮助我们进行分类。例如,看看内华达州公立高中的概况,标化考试分数就很有用。
问 去年夏天,最高法院推翻了平权法案。这件事如何影响达特茅斯学院对于标化考试政策的决定?在做决定时,你是否也考虑到了对考试要求的批评,比如标化考试阻碍了多样性和入学机会?
答 当然。但在过去的30年里,作为一名招生官员,我看到了不同高中之间的差异,也看到了美国教育的不平等,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更不用说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了。因此,我们将标化考试视为K-12不平衡的一种反映。我们并不是说它没有反映出这一点,但从背景上看,我们能够说:“这个分数告诉我们,它所产生的地方、学生所在的社区是怎样的?
我们如何利用它们来满足学生的需求?当你走遍这个国家,这个异质景观,它开始减轻一些关于考试有利于富人的批评。的确如此,但前提是你必须严格定义高分和低分。在有些地方,1700分(以旧版SAT为例,满分是2400)并不算高;在有些地方,1700分低于正常水平。而在另一些地方,它却非常高。1200分也是如此:有些地方的1200分闻所未闻,而有些地方的 1200 分则处于数据分布的末端。
在清晰阐明一切有关标化考试的问题这件事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并没有做到最好。在我们恢复标化考试要求的过程中,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报告达特茅斯学院的考试概况,让学生有更多机会看到:“哦,在我的情况下,这个分数真的很不错。”我认为这是另一个后疫情时代的宝贵机会。
这不仅仅是说,哦,前几年我们暂缓了标化考试要求,今年又突然恢复了,假装一切又回到了2019年。在过去的四个申请周期中,我们学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东西,我们已经将这种针对考试的情境化观点融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这么做了,但我们做到了。
问 疫情后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大学对当前申请人学术准备程度的信心,比如说成绩膨胀和学习损失的程度。这对这次的决定有多大影响?
答 这绝对是考虑因素之一。疫情对学习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难量化。但毫无疑问,高中和初中的线上学习是有影响的。至少在我所能观察到的申请人池子,这一点非常明显,我们遇到的学生在高中时成绩非常优异,并非个例,很多学生都拥有很亮眼的成绩单。
我并不是在批评这些高中,我只是认为,优秀学生的过剩,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进行评估。 在达特茅斯学院这所高选拔性的大学里,关于“如何在一群成绩优异的学生中做出高精确度的明智录取决定”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信息是宝贵的,为什么要遗留任何信息?我们并不是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你的命运。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是说我们不再重视成绩单和课程的完整性,这些仍然是我们评估过程的核心,但标化考试分数作为评估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问 作为一名资深的招生专家,你对考试的看法、标化考试要求、标化考试的好处、对考试的偏见,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
答 当然有。但考试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回想我早年参加SAT/ACT考试时,还有科目考试,或者更早的时候叫成就考试(Achievement Tests),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了。很多高中会有班级排名,但现在几乎完全没有了。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地被取消了。许多学区也不再报告GPA总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东西都消失了,标化考试还在,而且还有价值,因为很多其他重要的指标都消失了。
我们处于数据赤字的状态。与此同时,数据量也在增加。以塔夫茨大学为例,我刚到那里工作时,我们大约会收到13,000-14,000份申请,在我离开的时候,大约有20,000份,现在接近30,000份。随着申请量的增加,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审核时间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你如何在众多申请中做出明智的决定?
这时有些批评者就会说:“你不知道怎么做你的工作。”我知道怎么做我的工作,怎么审核学生的申请。但我需要能够遵循一些学业成绩的统计测量方法。每个人都需要对招生官员多一些信任,我们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多种视角来了解学生,我们正试图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做出最好的决定,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申请。
不过,即便以后媒体的关注逐渐褪去,这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政策会不断演变,我们会关注数据说明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我们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将标化考试作为我们审核流程的一部分,以一种透明的方式重新定义标化考试的含义,或许还能颠覆我们所坚持的一些传统观念。
这很重要,当我对高中辅导员说这些时,他们都说这很好。我们的担心在于招生人员是否会试图把一个分数塞进一个叙述中,但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分数的复杂性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