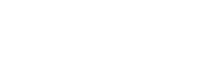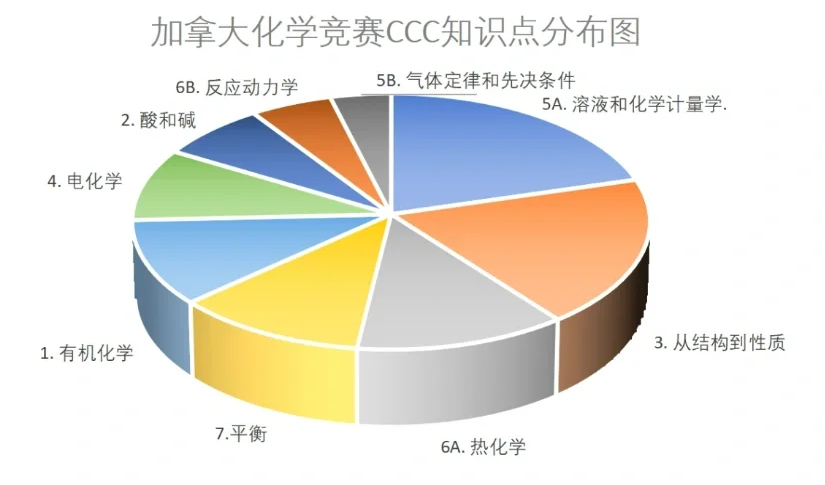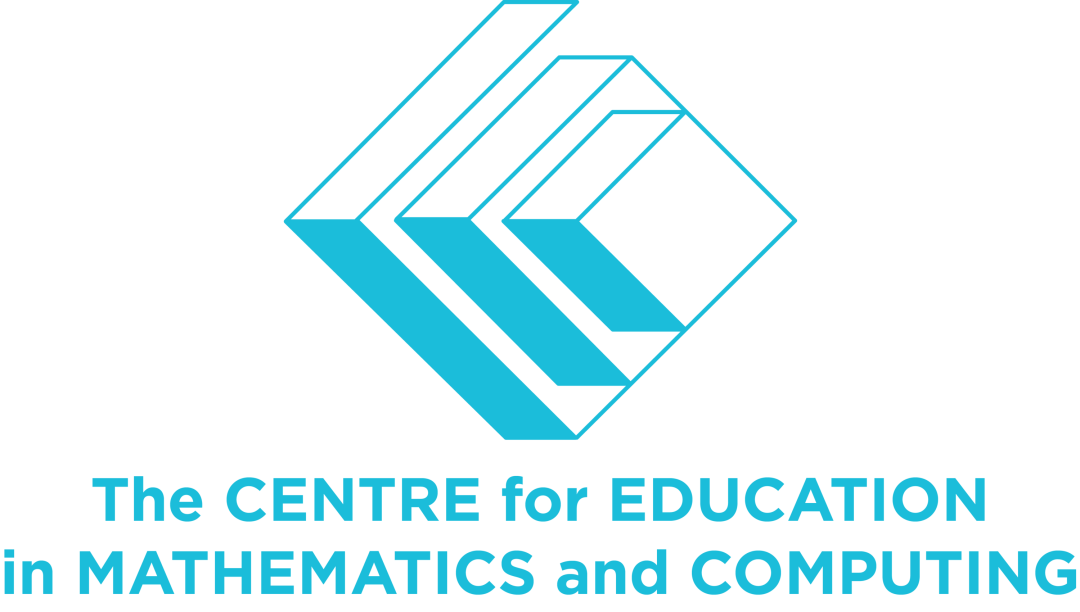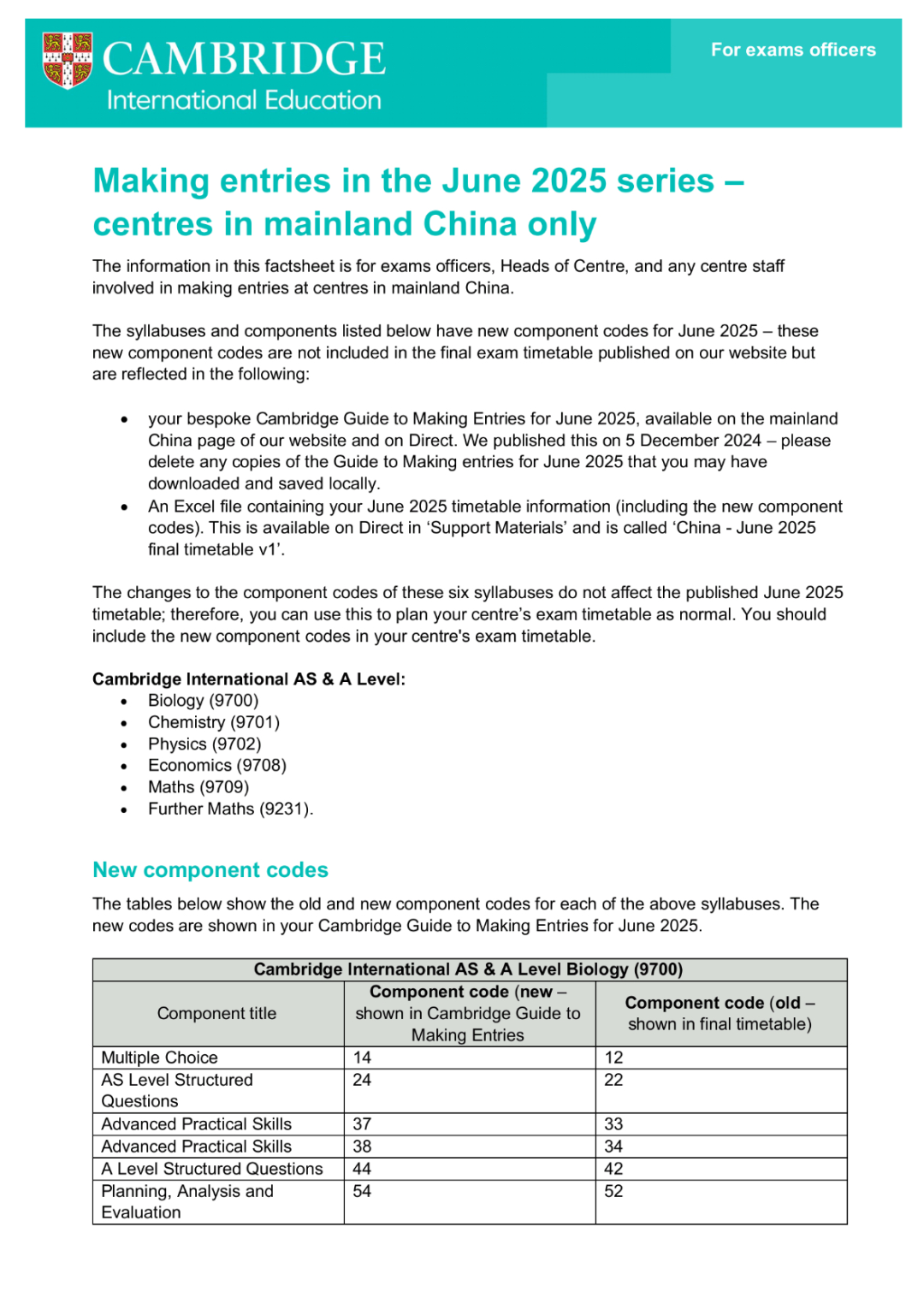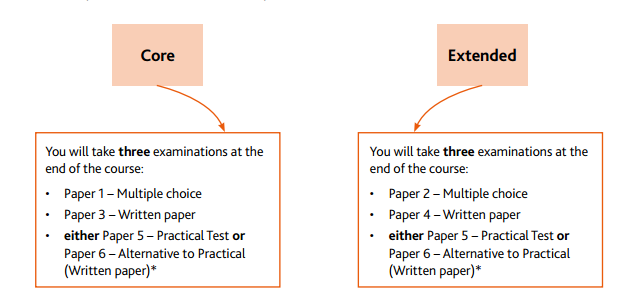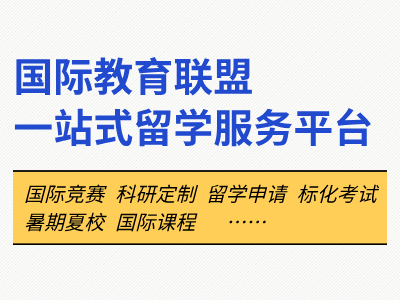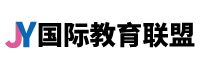关于如何正确使用“智能”工具,在现实社会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人们在职业场景中讨论技术飞升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机遇,以及如何不断学习才能掌控技术,然而这些话题一旦下放到教育场景,策略就“简单”了——高中生禁止使用手机,或者在监管之下使用智能产品(最好是不用)。
在国内大部分高中,“手机禁令”都是一种默认模式。有时候我们认为这多少有点本国特色,比如在一些美剧或英剧中,我们看到高中生的生活方式似乎更成人化,手机自由也更常态。
然而这并不代表在中国以外的国家,青少年的手机使用就不是问题。最近几个月,美国佛罗里达宣布在全州范围内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之后,这道禁令扩大成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内全天使用手机。而关于这道禁令的讨论,已经上升到一种全国教育界争论的问题。
这些争论帮助我们更深度理解“手机使用”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只有“禁令”,“手机使用”可能永远只是公共视野中的一个小问题,只要我们将青少年放在成人社会之外,或是边缘化,就可以“管控”处理;然而青少年终将会成为成人社会的主导者,让他们带着问题接管我们的时代,远不如我们与他们一起正视这些问题。
新问题出现与两种态度
此次佛罗里达州“手机禁令”的产生,源头是一系列社交霸凌问题的出现。
很多学校都出现了这样的事件:高中生策划了对同学的袭击,然后全程拍摄,将视频上传到TikTok和Instagram等平台,或是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接受挑战,参与“校园破坏”的竞赛。
同时,学校老师和校长还发现,在不禁止手机的情况下,学生在课堂不断向朋友发送消息,即时性聊天工具已经成为学习的最主要干扰因素。
无独有偶,美国加州橘子郡(Orange)教育工作者调研发现,疫情之后,青少年对手机的依恋正成为一种新现象,“在校园里,当学生穿过走廊,他们的视线很少离开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
疫情后的电子依赖、与现实生活隔绝、网络霸凌……很多关键词都在提醒手机使用的新问题,或者是早已存在,但愈加恶化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手机禁止”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立刻可做的事情。超出我们想象,实际上英美国家对青少年实行“手机禁止”的命令,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早,也更普遍,联合国教育和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国家目前制定了禁止或限制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法律或政策。
但持保留意见的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建议学校谨慎行事,“考虑新技术在学习中的作用,并将其政策建立在可靠的证据之上。”
“接触手机等数字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对新兴技术的批判性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学生需要了解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培养关键技能,并了解有或没有技术的生活。”“阻止学生接触新技术可能会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
手机禁令,还禁止了什么?
“手机禁令”最大的支持者,毫无疑问是学校和老师。在禁令推行的一段时期内,很多老师声称课堂互动情况有所改善,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积极性更高,且某学学科平均成绩有所提高。然而从更广泛的研究数据看来,手机禁令的结果只能是“好坏参半”。比如去年一项针对西班牙学校的研究发现,在实施手机禁令的两个学区,网络欺凌现象减少,数学和科学考试成绩也显著提高。
但更早些时候,2016年一项全美范围的校长调研显示,禁止使用手机的学校在网络欺凌发生率上高于允许使用手机的学校。而来自挪威的调研则显示,禁止手机之后,女生的平均成绩提升较高,但男生平均成绩没有变化。以上种种数据也许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关于手机使用的调研,并未形成一种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才使结果难以形成一种有说服力和建设性的共识。
但出乎意料的是,很多家长对“手机禁令”表示反对。大多数家长赞同在上课时间禁止手机,但觉得下课时禁止使用手机就“太过了”。今天的家长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手机帮助他们和孩子及时沟通一天的行程安排,“你在哪里?”“别忘了你放学还有足球课”“爸爸或妈妈会晚到,你在学校旁边的咖啡馆等我。”或者是孩子跟父母及时报告,“我因为某项作业被留在学校。”在家长看来:“如果孩子有手机,他们走路上学会更安全。”“手机会帮助孩子更加独立”“使用手机付款能让孩子学会负责任。”
但《纽约时报书评》主编帕梅拉·保罗看来,这些自认为的“好处”,只是父母对手机也有依赖,而且将很多育儿责任甩锅给了“手机”。“如果我们希望孩子独立、有责任感,这些品质是家长教出来的,而不是手机教出来的。”帕梅拉在专栏《父母更有手机问题》中这样评论,她认为“是太多父母认为,孩子需要一台手机”,而很多学校、学区手机禁令之所以无法落实下去,正是由于父母的这种态度。帕梅拉的观点有一些道理,但相同逻辑也可能用来反对手机禁令,比如我们也可以说:“是成年人世界应当教会青少年不要去用手机网络霸凌,而不是手机造成了这一切。”
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情况
在帕梅拉的专栏中,她引述一份来自Common Sense Media的新研究:97%的青少年和学龄前青少年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校期间使用手机的时间中位数为43分钟,主要用于社交媒体、游戏和 YouTube。
而在另一些调查中,一些青少年受访者则这样描述手机禁令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无法再使用手机在学校期间查看课程安排、在艺术课上拍摄自己的项目照片、在午餐时找到朋友,甚至无法添加新同学的电话号码到他们的联系人列表。
“想象一下,你每天用来与其他人交流的设备完全消失了,”一位13 岁的女孩说,“感觉完全孤立。”“被剥夺感”是手机禁令之下一些高中生非常直接的体验,而手机管控的方式也令很多学生,甚至教育工作者感觉这是教育本身的倒退,因为严查学生携带手机并不可能简单地做到“令行禁止”,因此佛罗里达州的学校必须派出专门的保安人员在校园里巡视,或是通过摄像头,将违禁使用手机的学生请出教室,进行惩罚。
也许学校的社交氛围会变得好一点,但“这也使得学校变得更像监狱”,一些关注佛州手机禁令的教育工作者这样评论,同时指出手机禁令下的一些盲点: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并不是每一个学生的生活都“封闭”在学习之中,有些孩子已经开始承担家庭责任,或是需要打工挣钱来负担自己的生活,而手机禁令不仅使他们错过重要消息,还使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接受违禁惩罚。
从青少年到成年,“阻断”问题真能解决问题吗?
以上种种有关青少年手机使用的监管、调研与争论,实际上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向,那就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处理这件事。从极端角度去看,手机与社交网络的不当使用,使青少年犯罪大幅增加,这可能是“手机禁令”实施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但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糟糕的也是犯罪本身,以及成年人为社交网络设计的规则,而非青少年使用手机这一行为。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那样,教会青少年识别网络风险,建立正向的行为导向,这是帮助青少年与数字化世界共存的根本,而非通过“阻断”的方式,让问题暂缓(留到他们成年之后再去犯错)。
相比禁止、没收、惩罚,“教化”当然是更难的路,但因为这很难,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简单、粗暴的方式?而在“手机禁令”这个典型问题上,仍然反映出时代教育的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学校与生活的脱节。
手机是当今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在大多数人看来,学校其实不必踏进现实生活,学习同样如此,这才是“手机禁令”可以轻易推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