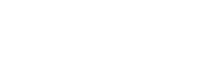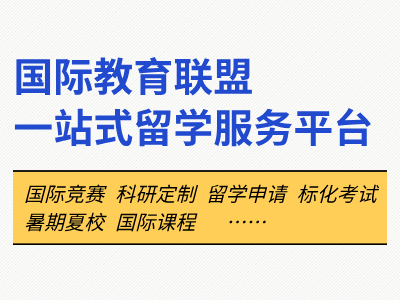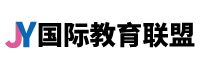距离上一次采访,我们与怡章已经阔别5年,此时的他即将从UCL毕业了。五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期限,足够考验一个人的初心,足够让人褪去青涩,也足够让人对自己产生全新的理解。
2017年是怡章辩论旅途的起点。那时恰是初二,他已经为去英国留学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骤然迎来闲暇时光的他,经一位在NHSDLC打美辩的朋友推荐也开始尝试打辩论。意外的是,他的第一次比赛就是2017年的国赛。
PF初试就是“hard模式”自然十分考验意志,但好在有队友相互扶持:“这场比赛对我而言是特殊的,第一次就是国赛。其实作为刚刚接触美辩的阶段,我只是很浅显地了解了辩论的框架,对于内容其实没什么很清晰地思路。但是那一次比赛也让我真正开始感受到了美辩的魅力,觉得很有意思。”
以初中生的年纪参加高中组的比赛、辩龄相对较短、起始难度又高,“debuff叠满”的情况下让怡章一度感到压力很大:“你会发现很多辩手可能从小学就开始打辩论了,看着小其实辩龄很长了,我之前遇到过两位天津的辩手,他们俩就是小学生但是打得非常好。”差距一下子被拉开,想要追赶上其他辩手的水平似乎路远迢迢,不过怡章很快就摆正了心态:“这种事情没法调整只能接受,你能做的就是慢慢地把能做到的事做好。”2017年,怡章在辩论的赛道上一路狂奔,一年时间里他足足打了11场比赛,成绩斐然,称得上是“最强杯子户”了。而他仿佛不知疲倦般地持续活跃在赛场上,原因唯有「乐在其中」:“还是因为喜欢吧,我挺享受辩论这件事儿的。”
更重要的是,在怡章看来,辩论就像运动一样,遵守着它独特的“能力守恒定律:“你付出了多少就会收获多少,每一滴汗水在未来都会以另一个姿态回到我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过程。”就像比赛有胜负,但都一定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成长——胜利带来的是喜悦和成就感,失败带来的是更强的抗挫折能力和韧性。
虽然热爱辩论,但对怡章来说,因辩论而牺牲学习和生活是不明智的:“实话说,选择正确的时机很重要。我认识一些非常勤奋的辩手,他们能去打比赛的时间都去了,但对我自己来说可能做不到像他们这样。我个人是觉得「平衡」很重要,比如我初三这段时间比较空一些我就用来辩论,就是说你得明确你什么时候想辩论,什么时候可以打辩论。
似乎是命运使然,怡章的第一场比赛是国赛,出国前的最后一场也是国赛。这一次他们走到了16强,而他用了“惨烈”一词来形容当时的战况:“那一次我们准备得很充分,彼此磨合得也很好,经过一年的历练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是那次国赛就很惨烈,印象里那个赛季的排名前10的辩手,我认识的很多非常优秀的辩手都在16强一口气输了。到那一阵子,对我来说可能并不是单纯地在辩论了,更像是一群朋友一起在做一件事,这样的结果挺让人遗憾的,但后来发现也还好,毕竟这些事是没办法强求的。”
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经历离别。辩论场上的离别似乎格外早一些、多一些,怡章明白比起困顿于一时的挫折,去全国各地打比赛时车窗外的风景、因辩论而相聚的队友和对手,以及这一段充实快乐的时光,更加值得自己珍惜:“其实我们都是因为辩论才有机会短暂地聚到一起,可以说是相聚短暂而分别长久的朋友吧,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打完比赛就又都分开了。这个缘分是非常珍贵的,大家一定要珍惜队友。”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队友之间的惺惺相惜、对手之间的势均力敌,那些在赛场上你来我往的激战,是怡章记忆中永远闪光的瞬间。

暂别赛场,怡章在英国开始了新的旅程,那是一段悠然的专注于读书的时光。虽然学校有些偏远,但胜在安静惬意,偶尔他也会坐火车去热闹些的地方走走。时光倏然而过,高二逐渐为申请学校忙碌了起来:“回过头看还是觉得自己当时有些地方没能做得更好。每个学校都有一定的偏好,比如说牛津的就非常看中“学术热情”。大家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结合学校的标准、自身条件和综合的概率因素,就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由于高中并没有浓厚的辩论氛围也没有好的社团,这两年中,怡章几乎没有机会再接触到辩论。直到顺利升入UCL后,他和辩论的缘分又开始续写。
“我有一个朋友Betty,她是有一年的国赛冠军,当时她跟我说‘等你到了大学一定要去打一打BP’,刚好我到UCL之后还没有想好要报什么社团,就想到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加入辩论社,小试一下BP。”很快,他就参加了自己的第一场BP赛事——北大Pro-AM,并且夺得了4强的名次:“试了一次之后我就发现我想要一直去做这件事,不是说为了提升口语表达、语言效率等等这些目的去做,而是我纯粹地喜欢和享受打辩论的感觉。”然而辩种不同,辩论的逻辑、方式也会随之产生巨大的变化,从PF切换至BP,一切又需要重新开始。
“有段时间我觉得出成绩很困难。”这是后来所有问题的起因,如果用怡章的话来总结那段“万分折磨”的适应期,那就是:“我觉得打BP是个特别痛苦的自我审视过程。”他将问题归结于「功利心」。伴随着比赛和训练中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好胜心也在悄悄膨胀:“带着如此高的期待去比赛往往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和遗憾。”对于结果的狂热追求让他一度遗忘了自己享受辩论的初心,而过高的期待和未达标的结果则成为了“痛苦”的根源。
BP让怡章在人生的初始阶段就了自我审视,虽痛苦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当他重新找回初心、明确了自己的道路后,必将得到蜕变:“一方面要去考虑是否赛前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与其他选手有过深度接触了以后有没有对自己的新认识?另外一方面,自己参与比赛的初衷是否出现了问题?是否过于关注获胜的结果,比如所谓的简历提升,而忽略了参与辩论的初衷?是否过于关注夸大其词而忘记了构建清晰的逻辑和引发思考,才是辩论最初的目的。”通过层层的自我剖析,怡章学会了放低期待并付出更多的努力,通过合理的时间规划来支配辩论,而不是让辩论支配自己的生活。

经历了一场痛苦蜕变后,怡章在辩论的领域中更向前迈了一步,不仅作为辩手活跃在赛场上,也开始尝试做BP裁判、竞选辩论社副社长、组织比赛。此时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BP比赛不单单是一个竞技的空间,更是让不同的声音被听到的舞台。
“你会发现,很多我们觉得会不会很难请的大佬或者学者,他们其实很看重这样的平台,希望有一个机会去和不同的观点对话的同时,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自己的看法被更多的人了解。所以如果档期不冲突的情况下,很多人是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的。像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关于教育的议题,当时是邀请到了英国当地三个比较大的私立教育协会的主席。不过他们的行程都非常繁忙,作为组织者,我们必须要提早半年甚至更早通过邮件去跟他们询问、敲时间。”然而,现实并不是开了金手指的爽文,尽管活动频率并不算太高——每三周一次,一次1-2小时——但实际上的准备工作却十分繁琐复杂,怡章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思及此处,怡章忍不住大大叹了一口气:“平衡,大概是这辈子最让我觉得困难的事情了,没有遇到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没有老师管理社团的情况下,作为副社长,怡章需要管人、管钱、管事;而作为比赛组织者,又要平衡辩手、嘉宾、工作人员,时常就遇到众口难调的情况:“比如原本拟定的辩题,可能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或者人群,我们自己内部会想着是不是需要更谨慎一点再讨论一下甚至是换一个辩题;再比如我们去邀约一个嘉宾,他可能对另外的嘉宾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等等,你猜不到最后在哪个环节会出现意外。”虽然并非万事尽如人意,常常让人倍感折磨,但怡章从未曾因此而动摇:“既然要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应该去付出相应的准备和努力。”
为了规避邀约被拒的风险,即使最终的邀约人数仅有4-6位嘉宾,他还是需要准备80人左右的拟邀约名单,一个个去沟通询问:“这个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邮件习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高效简洁,不需要太多的客套寒暄,你要知道自己该给谁发、发什么内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很宝贵,更希望能够直观地看到关键信息——什么时候在哪里做什么,最后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及时follow up,让他们知道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
从台上的辩手到台下的裁判,从台前的参与者到幕后的组织者,随着身份与视角的变换,怡章仿佛已经从学生的身份毕业,在处理棘手而繁杂的问题的过程中,提前经历了一场由BP带来的「自我社会化」历练:“我觉得管理的过程跟做领导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管理就是去平衡不一样的想法。整个管理辩论社包括组织活动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跳出学生思维的锻炼,赋予了我一个更适应社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更注重效率和结果的处事准则,这对未来我继续读研或找工作也是非常大的帮助。”5年的时间里,怡章完成了去伪存真的自我沉淀,而下一个5年,他玩笑道:“谁说得准未来呢?顺其自然就好。”前路漫漫,惟愿灿灿。